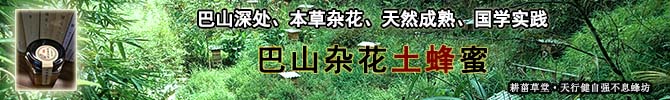◎ 国学经典书架——《中庸说》 [南宋] 张九成 著
| 卷一 卷二 卷三 跋 张九成 |
◎ 《中庸说》卷一 [回目录]
无垢先生范阳张九成
中庸说
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和即庸也。变和为庸,以言天下之定理不可易也。此一篇,子思所闻于曾子,圣道之尤粹者也,学者不可以不思。
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性、道、教三者之难名也久矣。子思传曾子之道,以其所践履而自得者,为天下后世,别白而言之,使学者知所适从焉,其有功于名教也大矣。天命之谓性,此指性之本体而言也。率性之谓道,此指人之求道而言也。修道之谓教,此指道之运用而言也。天命之谓性,第赞性之可贵耳,未见人收之为己物也。率性之谓道,则人体之为己物,而入于仁义礼智中矣,然而未见其设施运用也。修道之谓教,则仁行于父子,义行于君臣,礼行于宾主,智行于贤者,而道之等降隆杀于是而见焉。《中庸》之名,立于此三者矣。天命之谓性,喜怒哀乐未发以前者也,所以谓之中。率性之谓道,此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,以养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之理,此所以求中也。至于修道之谓教,则以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而见于用,发而皆中节矣,所以谓之庸也。子思立此三句,非见入深微,学臻圣地,其能为此言乎?盛矣哉!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此言道之所以为道也。夫率性之谓道,则舍性而求道,皆非所谓道也。是则君子之求道,岂可须臾舍性而求哉?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可也。使其不睹不闻处,微有私意间之,则非性之本位,而堕于人欲矣。人欲岂道也哉?故曰可离非道也。盖当其离处,即是非道,此率性所以谓之道。
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,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此指以率性之路,不可须臾离之义也。惟性不可须臾离,故于不睹不闻处每致意焉。夫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,况于稠人广众,合堂同席之间,其有不戒慎恐惧者乎?此正合内外之道,不可须臾离之本也。夫不睹不闻,少致其忽,宜若无害矣。然而怠忽之心,巳显见于心目之间,昭昭乎不可掩也。其精神所发,道理所形,亦必有非心邪气杂于其间,不足以感人动物,而招非意之辱,求莫为之祸焉。此君子所以慎其独也。诚诸中,形诸外,不可掩如此。呜呼,其可忽哉!惟一意戒慎恐惧,以养喜怒哀乐未发以前之理,此善求中之道也。
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
中,衍天命之义,和,衍修道之义。喜怒哀乐之未发,此指言性也,故谓之中。发而皆中节,此所谓发也,故谓之和。中指性言,故为大本;和指教言,故为达道。未发以前,戒慎恐惧,无一毫私欲。巳发之后,人伦之序,无一毫差失,此天地万物之宗也。所以言天地位于此,万物育于此。呜呼!天地万物皆在吾中和中,则中和之用亦大矣。学者不可不勉。仲尼曰: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时中,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无忌惮也。天命之谓性。此所谓中也。率性之谓道。此所以养中也。修道之谓教。此所谓庸也。当喜怒哀乐未发以前。君子戒慎恐惧。此率性也。及喜怒哀乐巳发之后。君子行人伦之序。此修道也。夫方当率性时。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处,此学者之事也。及其深入性之本原,直造所谓天命者在我,然后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教,以幸于天下。至于此时,圣人之功用兴矣,此所以谓之中庸也。然而君子小人名虽不同,岂无喜怒哀乐乎?喜怒哀乐未发时,君子则恐惧戒慎以率之,小人则何所不至哉,岂知所谓率也?喜怒哀乐巳发时,君子则出为君臣父子兄弟之教,小人则入于放辟邪侈矣,岂知所谓修也?谓小人无中庸之本则不可,谓小人能行《中庸》又不可,此不可不辨也。然而喜怒哀乐巳发之后,则谓之和,和何自而来哉?自中而巳矣。中既为和,则不得谓之中矣。不谓之中而谓之和,似于潜养之功为弗著也,故谓之时中,以言和自中来也。时中即和也。盖中不可执一也,以时而巳矣。如时可以仕则仕为中,时可以止则止为中,可以速,可以久,皆以时而为中,中不可执一也如此。且合天下而论之,则洛为中。自燕而望洛,则燕自有中也,而洛为偏矣。自越而望洛,则越自有中也,而洛亦为偏矣。故处天下时,则当以洛为中。至于处燕越之地,各中其所谓中可也,岂可以执一哉?此所以谓之时中也。小人乐闻时中之说,乃同乎荒俗,合乎污世;时尚纵横,吾为苏、张;时尚虚无,吾为衍、晏。此窃时中之名,而略无忌惮者也,此所以为小人也。然则君子之学,其可不慎乎?夫率性之谓道既?谓之率,则是已发矣,安得谓之中也?曰:率之为言,以见无须臾离也。既未离本位,恶得谓之发乎?诚如是说,修道岂巳离性而为之哉?曰:吾尝言之矣。率性之谓道,此学者之事也。至于圣人,则自率性直造天命之本,于是有乾坤造化,制为人伦之序,以幸天下,此所谓和也,所谓天下之大本达!道所谓天地位,万物育,所以成《中庸》之名也。此不可以离不离名之也。其理微矣,不可不致思焉。子曰:中庸其至矣乎,民鲜能久矣。
戒慎恐惧以养其中,人伦之序以宣其和,惟圣人能终始之。至于寻常之人,一息之暂且不能安,而况久乎?夫天地位于此,万物育于此,《中庸》之为至德,可不言而喻也。
子曰: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,知者过之,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矣,贤者过之,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饮食也,鲜能知味也。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以养其中,则发而中节,必为人伦之序,以宣其和,此《中庸》之本也。然知者知之太过,而愚者又不及知焉。既巳知之太过,与夫不及知,其能行乎?此道之所以不行也。贤者行之太过,而不肖者又不及行焉。既行之太过与夫不及行,此道之所以卒不明也。夫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此养中之法也。太过于此,则失养中之法;不及乎此,安知养中之法?君子欲求中庸,要当于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中得味,则识中之本矣。若夫不能守此法,而用意过当,与夫一出一入而欲求中,是犹终日饮食而不知味也。味乎,味乎!当优游涵泳于不睹不闻时可也。
子曰:道其不行矣夫。子曰:舜其大知也与。舜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恶而扬善,执其两端,用其中于民,其斯以为舜乎!
知者过之,愚者不及,贤者过之,不肖者又不及。审如是,道其不行矣。夫岂有是理哉?自有行之者矣。行之者其谁耶?大舜而巳矣。舜所以为大知者,以知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以养其中而无过不及也。夫戒谨不睹,恐惧不闻,其所以为养中者,乃在心术之内也。至于形之于外,则变为好问好察迩言,隐恶扬善矣。尝试溯好问好察迩言、隐恶扬善之心而上之,即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之心也。戒慎恐惧以养此中,则无过不及之端。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恶而扬善此中,则亦无过不及矣。执过不及之端,而用其中于民,则民皆知戒慎不睹、恐惧不闻,其形之于外,则亦尽人之情也。好问好察迩言,隐恶扬善而不敢忽矣。舜之所以为知者,以能用戒慎恐惧之心变,而为好问好察迩言、隐恶扬善之实也。夫好问好察迩言,则尽人之情,不敢断以己意。隐恶扬善,则恶念消亡,善端融泄,其戒慎恐惧可知矣。此所以能尽《中庸》之道也。学者欲识《中庸》,当于舜观之。
子曰:人皆曰予知,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,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,择乎中庸,而不能期月守也。人皆用知于诠品是非,而不知用知于戒慎恐惧;人皆用知于机巧术数,而不知用知于喜怒哀乐未发巳发之间。惟不留意于戒慎恐惧,故曰自驱而入于罟获陷阱嗜欲贪鄙之中而不自知。惟不留意于喜怒哀乐未发巳发之间,故虽《中庸》之理潜见,而不能期月守也。使移诠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惧,其知孰大焉?使移机巧术数之心于喜怒哀乐未发已发之间,其知又孰大焉。此篇直指学者用知处,故举舜所以为大知之事在前,而又立此说于后,其左右表里发明中庸之学也切矣,学者当审之。
子曰:回之为人也,择乎中庸,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
人皆知机巧术数之为知,而不知择乎中庸,守以期月之为知,惟颜子则进乎此矣。此孔子所以称之于守以期月之后也。夫喜怒哀乐,巳发未发之间,所谓中庸也,差之毫釐,缪以千里,其可不精择之哉!颜子戒慎恐惧,超然悟未发已发之机,或于喜处,或于怒处,至于哀处乐处,一得天命之性,所谓善者,则深入其中。人欲都亡,我心皆丧,人第见其拳拳服膺而弗失耳,而不知颜子与天理为一,无一毫私欲横乎其间,而不识不知我真无有矣,而况人欲乎?此《中庸》之妙也。舜发于好问、好察迩言、隐恶扬善之间,而颜子深居乎服膺拳拳之内,盖所以表里之也,非深造自得,谁能识之?
子曰:天下国家可均也,爵禄可辞也,白刃可蹈也,中庸不可能也。均天下国家,辞爵禄,蹈白刃,感慨或能为之,此血气也,用以求中庸难矣。中庸不在血气中,惟戒慎不睹、恐惧不闻者能得之,故曰可均、可辞、可蹈,而不用此以能中庸也。有此则是血气,非中庸也。呜呼!余观于《易》,乃知中庸之难守也。且均天下国家,辞爵禄,壮哉其勇也,而非所谓大壮。《易》曰:雷在天上,《大壮》。夫雷在天上,其壮为如何哉。然而君子体此壮以在心,止于非礼勿履而巳。是知均天下国家,辞爵禄,蹈白刃,未为壮而守中庸者之为壮也。且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即雷在天上,《大壮》也,即非礼勿履也,即《中庸》也,即天理也。其可以血气为之乎?惟血气消尽,《中庸》见矣。君子不可不察也。
子路问强。子曰:南方之强与?北方之强与?抑而强与?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,南方之强也,君子居之。祍金革,死而不厌,北方之强也,而强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哉矫!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。国有道,不变塞焉,强哉矫。国无道,至死不变,强哉矫。子路闻可均、可辞、可蹈、中庸不可能之语,以谓中庸之强,当如何。夫子知子路之所谓强者,不过血气耳。《中庸》之中,非血气所得停留者也,故设为三问,以斥血气之强。南方之强,北方之强,与夫子路之强,皆血气也,非中庸也。然而衽金革,死而不厌,谓之血气之强可也。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,君子居之,是亦足矣。乃谓之血气之强,何哉?盖强当从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中来,则此强为《中庸》之强。若乃山川风气使之如此,而中无所得焉,岂非血气云乎?子路天资好勇,其鼓琴也,流入北鄙,其言志也,则曰师旅。此北方之强也,故曰而强者居之。然则何以为中庸之强也?曰:和而不流,此喜怒哀乐之中节也,故其强矫然不挠。中立而不倚,此喜怒哀乐未发时也,故其强亦矫然不挠。惟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潜养中和,以至如此之强,故其见于用也,遇有道之世,则此中和不变于厄塞之节,故其强矫然不挠;遇无道之世,则此中和,胁之以死,而亦不变其节,故其强矫然不挠。夫不变者,乃不流不倚之发也。矫之为言,刚毅之貌,非矫揉之矫也。此一字系重轻,学者不可造次。夫《中庸》一以理为主,非从戒慎恐惧中来,安得如此之妙乎?其与血气之强相远矣。子路闻之,得不悼其平时之无益而潜养之不可巳乎?学者不欲遇天下之变则巳,如欲遇天下之变,其于中庸岂可不留意乎?
子曰:素隐行怪,后世有述焉,吾弗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,半涂而废,吾弗能巳矣。君子依乎中庸,遁世不见知而不悔,惟圣者能之。《中庸》之为德,不可作也,亦不可止也。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谓之作而非作,谓之止而非止,所以能养中庸也。素隐谓终身行乎隐晦,中庸在隐晦,则隐晦而巳矣,安可作也。傥微有作意,至行怪以钓名,则非中庸也。此圣人所以不为焉。遵道而行。谓率性也。中庸在率性。则率性而巳矣。安可止焉傥有止意至半涂而不进。则非中庸也。此圣人所以不巳焉。欲识《中庸》要处。请于弗为弗巳而味之。弗为弗己。即戒慎恐惧也。彼其半涂而废君子则依乎中庸。依则弗巳之谓。彼其素隐而行怪,君子则遁世不见知而不悔,不悔则弗为之谓。夫所以能不悔者,《中庸》之力也。故曰惟圣者能之。余尝求圣人而不可得,今乃知止在喜怒哀乐未发处耳,岂不近乎?子思明示天下人以入路,且曰: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圣人门庭荡荡明白如此,吾侪何为而不举鞭乎?学者宜慎思之,
君子之道费而隐。夫妇之愚,可以与知焉,及其至也,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,可以能行焉,及其至也,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君子之道,即中庸也。中庸不离喜怒哀乐未发巳发之间,此日用所不免者也。岂非费乎?费当为费用之费。虽夫妇之愚不肖,岂有无喜怒哀乐者乎?此所谓可以与知,可以能行者也。然而由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以养喜怒哀乐,使为中为和,以位天地,育万物,虽圣人犹皇皇汲汲,自谓有所不知,有所不能焉,岂非隐乎?盖自以为知,自以为能,则止矣,止非中庸也。惟若有所不知,有所不能,则戒慎恐惧,其敢一日而巳乎?此理微矣,力行者能识之,非口舌所能辨也。
《中庸说》卷第一。
◎ 《中庸说》卷二 [回目录]
中庸
天地之大也,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,天下莫能载焉;语小,天下莫能破焉。
此《中庸》之所以为大也。夫天地虽大,而不免有日月薄蚀,彗孛飞流,山川震动,草木倒植,寒暑失中,雨旸差序,水旱相继,札瘥流行,此人所以不免有憾也。然则财成其道,辅相其宜,弥纶范围,真有待于中庸耳,岂如中庸之君子。语其大则天地位焉。万物育焉。人岂有憾乎。此天下所以莫能载也。语其小则跂行喙息。蠉飞蠢动。皆待之以顺适。此天下所以莫能破也。夫中庸之道。赞天地之化育如此。而其要止在喜怒哀乐未发巳发之间而巳。而其所以入之之路。又止在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而巳。学者胡为不少致思乎?
《诗》云:鸢飞戾天,鱼跃于渊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,造端乎夫妇,及其至也,察乎天地。夫君子之道,所以大莫能载,小莫能破,以其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察于微茫之功也。戒慎恐惧,则于未形之先,未萌之始,巳致其察矣。察之之至,至于鸢飞鱼跃,而察乃在焉。夫能乱人之德而居人伦之先者,夫妇是也。欲识不睹不闻之实,当于夫妇而察之。故君子之察,必造端乎夫妇,使夫妇之道正,则天地之道皆正矣。其要如此,安可不察耶?察之如何,非心一形邪?意一作无不见其所自起,知其所由来,戒慎恐惧而不敢肆焉。察之既熟,岂特夫妇间哉?则凡象生于见,形起于微,上际下蟠,察无不在,所以如鸢之飞于天,如鱼之跃于渊,察乃随飞跃而见焉。而况日月星辰之运动,山川草木之流峙乎。顾惟此察。始于戒慎恐惧而巳。戒慎恐惧以养中和。而喜怒哀乐巳发未发之间。乃起而为中和。大含元气而天下莫能载。小入无间而天下莫能破。察之之功如此。君子于慎独之学。其可忽耶。子曰。道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,不可以为道。《诗》云:伐柯伐柯,其则不远。执柯以伐柯,睨而视之,犹以为远。
率性之谓道,道岂远人哉?人具有此性,又安可舍已之性而求道哉?性外无道,道外无性,舍人之性而欲求道,犹适越而北向,趋燕而南奔,虽驾骏马,乘轻车,卒岁穷年,殆见其无所得耳。夫执柯以伐柯,可谓近矣,然而犹以为远者,以性较之也。若人之性,当几即是,因体即明,非两物也。伐柯而视柯,犹是两物也。柯外有柯,岂非远乎?若乃人即为道,不待它求,其与伐柯异矣。圣人明辨细微,至于如此,学者率性,其可不致精乎?
故君子以人治人,改而止,忠恕违道不远,施诸已而不愿,亦勿施于人,
人即性也。君子既率性而得道,天下之人有不由乎道者,以迷其性也。君子则以我之性觉彼之性,其寓之簠簋俎豆、制度文章,以至钟鼓管磬、竽笙环佩、元酒大羹、爇萧郁鬯之间者,无非觉其性也。使其由此以见性,则自然由乎中庸之道,而向来无物之言、不常之行,皆扫不见迹矣。夫君子所以区区如此者,止欲其率性由道而巳。既巳率性由道,复有何事哉?故得其改则止矣,此忠恕之道也。夫恕由忠而生,忠所以责己也。知己之难克,然后知天下之未见性者。不可深罪也。故人有平生为恶,使一见性本不蹈前辙,则君子止矣。不复更责矣。岂非忠恕乎。忠恕去道如此之近者,以施诸已而不愿,亦勿施于人而巳。且吾巳改过而率性,使人之责己尚不已,吾意岂不以其为太甚乎。《中庸》道中无太甚也。由是可以知圣人之存心。
君子之道四,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,以事父,未能也。所求乎臣,以事君,未能也。所求乎弟,以事兄,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,先施之未能也。君子由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深致其察,故其形于外也,如大舜之好问而好察迩言,隐恶而杨善,如颜子之择乎中庸,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,如诗人之察鸢飞鱼跃,如君子之察乎天地。故自不睹不闻处察之,以至于世间人情,无所不致其察。先察知一已之难克,而后察见天下皆为可恕之人,不敢妄责备焉。每事先求乎已之所能行者,然后推之以善天下。凡施诸己而不愿者,亦不敢以施诸人,而已之所愿者,则推而行之,与天下同其乐。此所以为《中庸》之道。而深原其功,乃自于戒慎恐惧以致其察之功也。明乎此说,则君子之道四:如子事父,臣事君,弟事兄,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,盖所以致其察也。人伦之大而致其察,则天下之理无遗余矣。察子之事父吾未能,安敢责父之爱子乎?察臣之事君,吾未能,安敢责君之礼臣乎?察弟之事兄,吾未能,安敢责兄之友弟乎。察朋友先施之吾未能。安敢责朋友之必信乎。此忠恕之道也。夫自以为能则止矣。故终身不能。自以谓未能。则皇皇汲汲其敢巳耶。如前言圣人有不知有不能。而此言未能。此意深矣。学者不可忽也。夫圣人常处于不知不能未能之地。以见其皇皇汲汲。无敢巳焉之意。此所以无所不知。无所不能。且于穆不已,天之所以为天,纯亦不已,文王之所以为文王。使圣人于君子之道四自以为能则巳矣。其责备于天下。岂不深乎。巳非天之理也。如韩愈作《诱里操》曰。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。此深见文王之心。臣以事君未能之意。舜祗载见瞽瞍负罪引慝,此亦子之事父未能之意。傥文王以为能则怼君,舜以为能则怨父,《中庸》之道于此二事可见矣。非于不睹不闻处深致其察,又乌能推之人伦若是其微哉。是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庸德之行,庸言之谨,有所不足,不敢不勉,有余不敢尽,言顾行,行顾言,君子胡不慥慥尔自戒慎恐惧,事致其察,其发见于忠恕。是故其为行也,则为庸德之行,其为言也,则为庸言之谨。庸者非不足,亦非有余,适当其可者是也。夫惟戒慎恐惧,则不足者不敢不勉以至于此,有余者不敢尽发以过于此,所谓中庸也。戒慎恐惧,则常致其察。是故当其言也,则于言察其行;当其行也,则于行察其言。顾者,察也。夫《中庸》之道如此,君子胡不戒慎恐惧,事致其察,以慥慥于此地乎?慥慥者,不已之谓也。
君子素其位而行,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,行乎富贵;素贫贱,行乎贫贱;素夷狄,行乎夷狄;素患难,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
忠恕之道,其至矣乎!尽其在我而不责于人。素其位而行,尽其在我也。不责备于人,不愿乎其外也。涵泳乎忠恕之中,郁如三春,薰如醇酎,何所往而不可乎。素犹雅素之素,舜之若将终身者是也。使终身富贵,则以忠恕之道行乎富贵,若尧是也。终身贫贱,则以忠恕之道行乎贫贱,若颜子是也。素夷狄,则以忠恕之道行乎夷狄,若箕子是也。素患难,则以忠恕之道行乎患难,若孔子是也。富贵贫贱,夷狄患难,皆天之所以命我者,吾其如之何哉,姑听之而巳矣。然吾有忠恕之道,无入而不自得,故尽其在我,不责备于人,是以戒慎恐惧,不敢使一毫私意介乎其心,而宽夷平易,优游怡愉,衎衎如也,融融如也,自得之道,概在乎此。呜呼,忠恕其至矣乎。
在上位不陵下,在下位不援上,正己而不求于人,则无怨。上不怨天,下不尤人。故君子居易以俟命,小人行险以侥幸。子曰:射有似乎君子,失诸正鹄,反求诸其身。此言君子自戒。慎不睹恐惧,不闻,酝酿成《中庸》之道。处上下天人之间,无所不用其忠恕也。其在上也,以忠恕待人,故不陵下;其在下也,以忠恕自处,故不援上。援者,欲己与之齐也。夫为上所陵,为下所援,而不以忠恕处其间,则不能无怨憾矣。君子力行忠恕之道,正己而不求于人,故处陵忽干援之中,其心泰然,无丝毫之怨,以至身行于贫贱忧患、祸难丧失不可堪处之间,一皆以忠恕为乐,若将终身于此而不动焉,夫何怨天尤人之有。此无他,君子居忠恕以应天命而巳。易者,忠恕之谓。若夫小人,则不能安于忠恕,至于丧名失节,以求合于上,卒不免于患难,徒使身名两失而已。此行险以徼幸者也。其所以如此者,以其平时不知慎独之学,不留意于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以养中庸之道,而察忠恕一贯之理耳。射有正鹄,宾射之侯则谓之正,大射之俟则谓之鹄。使吾内志正,外体直,持弓矢审固,则宾射必不出正,大射必栖于鹄,此必然之理也。使在我有杪忽之差,则在彼有寻丈之失矣。然则失诸正鹄,岂正鹄之罪哉?吾内志不正,外体不直,以至持弓矢不审固之罪也。犹之为上所陵,为下所援,不得处富贵安平,而每遇贫贱忧患,祸难丧失,若天所不佑,人所不归者,岂上下天人之罪哉?皆吾戒慎恐惧不至,而中和之理不发见,不足以感发天下之几也。使诚中和,天地且位于此,万物且育于此,况上下天人之间乎?诚知此理,方且戒慎恐惧,正已之不给,又何暇责备于人乎?此所以为中庸也。君子之道,譬如行远必自迩,譬如登高必自卑。《诗》曰:妻子好合,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,和乐且耽。宜尔室家,乐尔妻孥。子曰:父母其顺矣乎。此言君子推忠恕之效也。夫欲知戒慎不睹、恐惧不闻之效,当于忠恕卜之。欲知忠恕之效,当于父母卜之。使父母顺适,则忠恕之效著矣。故有登高行远之譬。夫行远必自迩,登高必自卑。妻子兄弟迩也,卑也。欲父母顺适,必自妻子合,兄弟和始,岂非父母高远,而妻子兄弟卑近乎?使妻子好合如鼓瑟琴,推之于兄弟,则兄弟既翕和乐且耽矣。夫人为人宜于室家,乐于妻拿,想其为人,曲尽在我之理,深识人情之微,庄肃恭谨,宽夷平易,以此心事父母,父母其有不顺乎。使其不知戒慎恐惧之理,待己甚轻,责人甚重,则于妻子必不合,于兄弟必不和。一家之内,妻子兄弟如此,父母岂得顺适乎?此不孝之子也。夫在妻子为合,在兄弟为和,在父母为顺,此一理也。今于妻子兄弟父母如此,原其所以,以不知忠恕之理也。不知忠恕之理,以不知戒慎不睹、恐惧不闻之理也。是以君子于慎独之学,不可须臾离。
子曰:鬼神之为德,其盛矣乎!视之而弗见,听之而弗闻,体物而不可遗,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,洋洋乎如在其上,如在其左右。《诗》曰:神之格思,不可度思,矧可射思。夫微之显,诚之不可掩如此夫,
鬼神在明则为《中庸》,《中庸》在幽则为鬼神,其实一也。明则有礼乐,幽则有鬼神是也。夫《中庸》之要处,在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而喜怒哀乐森列于中,不可欺者,此鬼神之德也。是以鬼神之德,虽曰视之而弗见,听之而弗闻,然天地万物森然鬼神列于中,不可遗也。惟鬼神之德如此,故足以发天下之敬,使皆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而齐戒以肃其身,明洁以敬其心,盛服以严其貌,洋洋乎如在其上,在其左右,岂敢有一毫私意哉?此正养《中庸》之几也。故引神之格思,不可度思,矧可射思为证。夫有度有射,皆私意耳,非戒慎恐惧,其可以享鬼神乎?夫鬼神弗见闻,而使人耸然不敢起,非心邪意,俨然如在者,则以《中庸》之道发于幽者,不得不尔。呜呼,微之显,诚之不可掩,其状乃如此。君子之于慎独,其可忽乎?子曰:舜其大孝也欤?德为圣人,尊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,必因其材而笃焉,故栽者培之,倾者覆之。《诗》曰:嘉乐君子,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,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,自天申之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夫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其见于舜也,内则以养中和,外则发之于好问,好察迩言,隐恶而扬善,与夫大孝之德。夫所以好问,所以好察,所以隐恶,所以扬善,所以为大孝,皆戒慎恐惧之形见也。此所谓诚诸中,形诸外,有不可得而巳者。夫舜负罪引慝,祗载见瞽瞍,夔夔齐栗,非戒慎恐惧之形见乎?此所以为大孝也。且应龙之翔,则云雾滃然而起,震风薄怒,则万空不约而号,使自戒慎恐惧,发而为大孝,以德则为圣人,以尊则为天子,以富则有四海之内,而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者,此必致之理也。夫何故?以大德必得,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,犹石韫美玉,则一山为之葱青,水怀明珠,则一川为之秀润。天理如此,何足怪哉。盖天之生万物,初无容心也,因其材而成之耳。如鸾凰为瑞物,自取尊荣,鸱枭为妖祥,自取弹射,楩楠自取栋梁,蒲柳自取薪爨,天亦因其材而成之耳,岂能有所损益哉。栽者本根深固,自取培益。倾者本根摇动,自取颠覆,亦岂有心哉。是以知大德者,自取位禄名寿,而无德者自取贫贱刑戮也。是位禄名寿,乃大德之形见也。不如是,是吾德之未至也。故引《嘉乐》之诗为证,而断之曰:大德必受命,其言判别不疑,此所以勉天下之为德者,当始于戒慎恐惧,而以位禄名寿以卜德之进否也。世之论者曰:孔子大圣人,而名位禄不著,颜子大贤,而寿亦不闻,斯言欺我哉。曰:学者读书,当识立言之体,方论大德受命之理,此天下之正理也,安得以孔颜为说?至于孔颜,可谓天理颠倒,事之不幸者也,岂可以为常谈哉。然而孔颜之位禄名寿,亦岂可诬也?虽不得志于当时,而万世之后,天子师事,巍然南面,尊主大国,合天下而拜之,大德者必受命,亦可知矣。君子第当论大孝大德如何。至于位禄名寿,至与不至,盍亦日日新,又日新,以警省其所未至乎?上以大舜当年为则,下以孔颜后世为准,岂不韪哉?
《中庸说》卷第二。
◎ 《中庸说》卷三 [回目录]
中庸
子曰:无忧者,其唯文王乎?以王季为父,以武王为子,父作之,子述之。
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则无适而不在中和,中和则无忧也必矣。古之人有享斯效者,其惟文王乎?夫中和之中,自当有贤父圣子,文王其见之矣。以王季为父,是父所作者中和也。以武王为子,是子所述者中和也。文王处贤父圣子之间,夫何忧哉!中和之见于人者,即文王可知矣。然则舜以瞽䀻为父,以商均为子,则中和将何处乎?曰:中和之见于人,当如文王之无忧。至于大舜父子,斯天伦之不幸也。不幸,岂可以为常乎!学者当知此意,中和之道无所疑矣。此不可不辩明焉。
武王缵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,壹戎衣而有天下,身不失天下之显名,尊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。
武王缵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,绪即中和也。天命巳逼,民心久遏,乃一戎商而有天下,呜呼,岂得巳哉。戎商宜若,非中和也,是何言欤。子思不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乎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,此怒之中节也,此中和也,此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也。然而武王之举危道也,圣人之不幸者也。其曰不失天下之显名,与必得之言相并,则知武王之举危道也,圣人之不幸也。然而又不失尊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者,则以出于中和,故其理当如是也。武王末受命,周公成文武之德,追王太王、王季,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,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,父为大夫,子为士,葬以大夫,𥙊以士;父为士,子为大夫,葬以士,𥙊以大夫。期之丧,达乎大夫;三年之丧,达乎天子父母之丧,无贵贱一也。
夫武王之中和,岂止行之于克殷一事而已哉?又于追王之事见之。夫追王乃中和所当然也。周公承文王、武王之中和,以行追王太王、王季之礼,与夫推追王之心,以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,又推追王之礼,以下达乎诸侯、大夫及士庶人,如父为士,子为大夫,葬以士,𥙊以大夫是也。夫士而受大夫之𥙊,此追王之意,下达于大夫也。使父为庶人,子为大夫,亦将葬以庶人,𥙊以大夫矣。此深察人子之心以致意于其先也。审如是,父为大夫,子为士,葬以大夫,𥙊以士,抑吾贬吾亲就士之礼耶?追王之意安在哉?曰:事各有称,葬以大夫,是丧从死者之义。𥙊以士,是𥙊从生者之义。以己之禄𥙊其先人,此意与追王之心一等也。惟深思者见之。傥以世俗之心,以荣辱吾亲,非中和之道也。至于期之丧,达乎大夫;三年之丧,达乎天子;父母之丧,无贵贱一也,皆喜怒哀乐已发之中节者也。此天理之自然者,不可加损焉。惟事事隐之于心,如追王,如𥙊以,天子如达乎?诸侯达乎?大夫,达乎天子,无贵贱一也,皆轻重中节,天理自然,无一毫私意偏倚于其间。中和之形见于作用者如此,不可不致精以求之也。至于论名数之意,吕与叔辩之甚详,此不复叙。
子曰: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。夫孝者,善继人之志,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修其祖庙,陈其宗器,设其裳衣,荐其时食。宗庙之礼,所以序昭𥡆也。序爵,所以辨贵贱也。序事,所以辨贤也。旅酬下为上,所以逮贱也。燕毛,所以序齿也。践其位,行其礼,奏其乐,敬其所尊,爱其所亲,事死如事生,事亡如事存,孝之至也。
祖庙宗器。裳衣时食、昭𥡆贵贱,辨贤逮贱,序齿践位,行礼奏乐,敬尊爱亲,事死事亡,虽施设隐显未详,然皆文王中和之所发见,寓于心志事为之间者如此。此文王之志,文王之事也。继志述事者无他,第于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处,致其察,以养中和之理,然后深见文王之所为,一一皆天理中发见者,随时损益而不忘其中和之大,此文王之志,文王之事所以望于武王、周公者,而武王周公所以为达者,亦正以是也。此所以反复具载于此篇,则以中庸之德当如是也。若夫名数之学,精微之义,则吕与叔龟山先生辩之甚详,此不复叙。
郊社之礼,所以事上帝也,宗庙之礼,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,禘尝之义,治国其如示诸掌乎。
郊社之礼,宗庙之礼,皆自中和中出,岂私智所为哉。夫郊社之礼,禘尝之义,此先王深知天神地示人鬼之心,而即国外之郊以祀天,国中之社以𥙊地,禘尝之礼以享鬼神。不知先王居于何地,知天神自郊求,地示自社求,人鬼自禘尝求哉?夫其数可陈也,其义难知也。明乎郊社之礼,禘尝之义,治天下国家,直推此而为之耳。然而礼义径自何而明哉?惟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以养中和,则天神地示、人鬼之心,皆见于此矣。且天地位于此,万物育于此,治国岂能出此理哉?是以君子慎其独也。
哀公问政,子曰:文武之政,布在方策,其人存,则其政举,其人亡,则其政息。人道敏政,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,蒲卢也。
文武之政,即中和也。布在《方策》书,此中和也。有中和之君子,则见文武之心,故其政举无中和之人。虽如《方策》所言,一一行之,若《王莽传》中所载井田赋禄之政,无不依三代制作。然篡逆之臣,岂尝梦见中和?是以一切颠倒,天下大乱,适以资笑具而巳。则其政息。复何疑哉。夫使人诚得中和之道。则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颦笑之间。天下巳丕𠮓矣。人道敏政。犹之地道焉。布种下实。未及顷刻日夜之息。一经雨露之润。则勃然而生。为萌为芽。为𠏉为枝为叶。以至为华为实。向来荒虚之地。一旦青葱秀润,可揽可掬矣。以地道敏树观之,则人道敏政可见也。盖地道亦巳得中和故也。然政之𠮓化,何止如地道哉?系乎其人如何耳。尧舜率天下以仁,则人人如尧舜,而比屋可封;桀纣率天下以暴,则人人如桀纣,而比屋可诛,真如蒲卢取螟蛉祝之曰:类我类我久,则皆似之矣。使以中和布之于政,发起天下之中和,则江汉之女无思犯礼,兔置之人莫不好德,人人有士君子之行,不难到也。此所以载此章于《中庸》焉。
故为政在人,取人以身,修身以道,修道以仁。仁者人也,亲亲为大;义者宜也,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,尊贤之等,礼所生也。在下位不获乎上,民不可得而治矣。
政如蒲卢,蒲卢祝螟蛉,则螟蛉𠮓为蒲卢矣。为政岂不在中和之人乎?有中和之人,则有中和之政。取中和之人,则当以身为则。身中和,则取人亦中和矣。然则何以致身之中和哉。戒慎不睹。恐惧不闻。以率性可也。率性之谓道。故修身以道。即中和见矣。然仁者人也。亲亲为大。义者宜也。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。尊贤之等。隆杀等降。有品节焉。一出于仁义而巳矣。仁。人心也。义人路也。义自仁中出。路自心中来。则所谓义又出于仁也。惟仁有品节焉。此修道以仁也。仁者。人也。义者宜也。其意安在。曰。非矜私意。非行小慧,坦然与天下同其功者,此仁也。而其用莫大于亲亲。不高以绝物。不卑以累己。适然得万事之理者。此义也。而其用莫大于尊贤。亲有上下,故有隆杀;贤有小大,故有等级。隆杀等级,礼自此而生矣。此所谓教也。修道之谓教,其是之谓欤。然则中和之理,何在而不然哉?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,思修身,不可以不事亲;思事亲,不可以不知人;思知人,不可以不知天。夫欲行文武之政,不可以无人,而取人当以身。故身不可以不修。修身以何为?则以事亲为则。事亲以何为则?以知人为则。知人以何为?则以知天为则。何谓天?喜怒哀乐未发以前,天也。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。于不睹不闻处,深致其察,所以知天也。推知天之心,以知人,则人之幽隐深微无不察矣,故贤不肖洞然不可乱。推知人之心以事亲,则亲之幽隐深微无不察矣,故能先意承志,先事几谏,而事亲得其道也。事亲得其道,则修身之效也。修身既效,则以此中和识天下之中和矣,故能取天下中和之人,以行文武中和之政。然则子思首之以天命之谓性,意乃在此,其言岂不深密乎。学者其可以易而观之哉。天下之达道五,所以行之者三,曰君臣也,父子也,夫妇也,昆弟也,朋友之交也。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勇三者,天下之达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,或学而知之,或困而知之,及其知之,一也。或安而行之,或利而行之,或勉强而行之,及其成功,一也。
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是君臣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交,皆和之所发见也,故谓之达道智,知此理而行仁,觉此理而行勇,决此理而行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交,天下之所同,故谓之达道。知仁勇,一己所自得,故谓之达德。所以行君臣父子五者,在知仁勇,所以行知仁勇者,在诚。一者,诚也,诚即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是也。夫是诚也,或生而知之,若尧舜是,或学而知之,若汤武是;或困而知之,若太甲是。所以知之者何物哉?诚也,知之耳,吾未能有行焉,是未能运用此诚也。然有安而行之者,亦若尧舜是;有利而行之者,亦若汤武是;有勉强而行之者,亦若太甲是。夫行之者其何物哉?亦诚也。是行达道者,知仁、勇,行知、仁、勇者诚;知诚者诚,行诚者诚。夫诚一耳,何为行知、仁、勇者诚,而又知诚者诚,行诚者亦诚哉?此盖有说也。其说安在?曰:行知、仁、勇者,诚也。以谓诚如是尽矣,而所以知此诚者其谁乎?即诚也。知之耳,未及行也。所以行此诚者其谁乎?即诚也。此圣人极诚之所在而指之也。行知仁勇者诚,知诚者将以为它物耳,又是诚耳。知未及行,行诚者又将以为它物耳,又是诚耳。诚字虽同,而行知仁勇之诚,不若知诚之诚为甚明,知诚之诚,又不若行诚之诚为甚大也。呜呼!诚之为物,如此,其可以浅易窥之哉。此于𥡆不巳,天之所以为天纯,亦不已,文王之所以为文王也,其深矣哉。子曰: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,则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修身,则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,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行达道者,知仁勇。知仁勇自何而入哉。此圣人所以又指以入知仁勇之路也。夫好学必有所见而然也,故谓之知。力行必以不能自巳而然也,故谓之仁。知耻必断然不为也,故谓之勇。然而不直指好学为知,力行为仁,知耻为勇,而曰近者何也。近之为言,以言不远也。不远即在此而巳矣。第知所以好学者谁,所以力行者谁,所以知耻者谁,则为知为仁为勇矣。夫见于言语文字者,皆近之而巳矣。唯人体之,识所以体之者为谁,当几而明,即事而解,则知仁勇岂他物哉。知斯三者,则直趋知仁勇之路,身岂有不修哉?知所以修身,则于天下之人皆当开导之,使自趋知仁勇之路。知仁勇,天下所同有也。故知所以修身,则知所以治人。知治人之路,不出乎知仁勇,则周旋四顾,其所以治天下国家,亦不出乎知仁勇之路而巳。呜呼!岂不简易明白乎?夫所谓学,所谓行,所谓耻,何也?即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之谓。学者不于此入,则泛然如萍之在水,逢风南北,有何所寄泊乎?此君子所以慎其独也。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,曰修身也,尊贤也,亲亲也,敬大臣也,体群臣也,子庶民也,来百工也,柔远人也,怀诸侯也。
夫知、知、仁、勇,则知所以修身。推而极之,以至于治天下国家。其为天下国家也,则散而为《九经》。《九经》则知、仁、勇之用也。夫时当孟春,则不期而鱼上冰,獭祭鱼,鸿雁来矣。时当孟夏,则不期而蝼蝈鸣,蚯蚓出,王瓜生,苦菜秀矣。岂孟春、孟夏区区号令于鱼獭、鸿雁、蝼蝈、蚯蚓、王瓜、苦菜哉?一气之行,其法当如是耳。审乎此,使不知知、仁、勇则巳,如其知知仁勇发于为天下国家,则亦不期修身尊贤、亲亲,敬大臣,体群臣,子庶民,来百工,柔远人,怀诸侯矣。使一事不备,必知仁、勇,未尽其道也。诚使知仁勇皆尽其道,则此九经以次而行,不先不后,不迟不速,皆中其会矣。此天理之自然,非私智所能为也。呜呼,从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发为知仁勇,其极施于天下国家如此。然则中庸之为德,其至矣乎之言一一见矣,岂欺我哉。然而知知仁勇三者,则知所以修身,以至知所以治天下国家。今为天下国家,又先曰修身。夫前言修身则能治天下国家,今为天下国家又曰修身,何也?曰:《中庸》之道无止法也。此又于𥡆不已,纯亦不已之意,唯力学者乃能识之。
修身则道立,尊贤则不惑,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,敬大臣则不眩,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,子庶民则百姓劝,来百工则财用足,柔远人则四方归之,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
夫自中和之理,发于君臣、父子、昆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,𠮓其名为知、仁、勇,又𠮓其名为一,又𠮓其所以达道者为《九经》,皆中和之作用,无往而不中节也。夫惟中节,故以之修身则道立,以之尊贤则不惑,以之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,以之敬大臣则不眩,以之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。体,若《四牡》之诗所谓有功而见知则说是也。知谓体悉之也。以之子庶民则百姓劝,以之来百工则财用足,以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,以之怀诸侯,则天下畏之。夫所以立,所以不惑,不怨不眩,所以报礼重,所以劝,所以足,所以归,所以畏,是乃中和之中节,故其效自尔也。使吾修身而道未立,吾亲亲而怨以至,吾怀诸侯而不畏,是吾于中和未至其极也。且致中和则天地位于此,万物育于此,《九经》其有不效乎?此君子所以慎其独也。
《中庸说》卷第三。
右五行,原题在卷一首叶及卷二末叶,移录於此。编者识。
贰册之内,宝永三年丙戌八月良辰,龙菖首座代,龙奭修褙焉。
◎ 《中庸说》跋 [回目录]
余祖文忠公正色立朝,敦尚气节,为有宋名臣,著书垂教,卷帙宏富。其见于《宋艺文志》者,《尚书详说》五十卷,《中庸说》一卷,《大学说》一卷,《孝经解》四卷,《论语解》十卷,《乡党少仪》《咸有一德论》、《孟子拾遗》共一卷,《心传录》十二卷,《语录》十四卷。见于《郡斋读书志》者,《孟子解》三十六卷,《唐鲙》五十卷。见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者,《论语拾遗》一卷,《言行编》、《遗文》共一卷。见于《玉海》者,重修《神宗实录》二百卷。见于家传者,《经筵讲义》一卷,《横浦家集》二十卷。杂见他书者,《书传统论》六卷,《春秋讲义》一卷。标注《国语类编》及《唐诗》,该无卷数,其书名卷数微异者不复举。今四库著录,惟《孟子传》残本二十九卷,《横浦集》二十卷,其乡党少仪《咸有一德论》、《孟子拾遗》、《心传录》、《书传统论》、《春秋讲义》即附载《横浦集》中,其他均不传。日本涩江全善《经籍访古志》有宋椠《中庸说》六卷,藏普门院。余求之有年,不知其所在。岁戊辰东渡,故人内藤湖南语余:院在京都东福寺既睹。其书已佚后半。请于寺僧。摄影携归。才四十叶耳。曩读《朱文公集》。谓公以佛语释儒书。驳斥是书者。殆及万言。其征引原文均合。盖此即朱子所见之本。公之为学。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。求其内心。有得勿止。更求其发而中节之用,其途径与朱子容有不同。孰是孰非,非余所敢议。余独痛夫儒释之辨盛于当日,公之学说为朱子所抨击,致湮没而不彰。是书亦自宋迄今,无复刊行。余既得诸海外,因覆印以饷今之学者,且冀其因有异同而得并存焉,则幸甚矣。《民国纪》元二十有五年丙子四月,裔孙元济谨识。